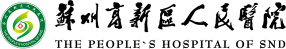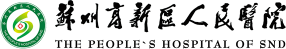【读书月征文】王小波与存在主义哲学 ——读《黄金时代》有感(徐珺)
我很喜欢看《见字如面》这个节目,有一期讲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峰开了一份“不必读”书单。他认为“绝大多数从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,不必读”,这一阶段的作品时代烙印太强,缺少人性的真实面。然而,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应不是那“绝大多数”,它有别于那个年代的任何文学作品。
这个以上山下乡为背景的作品,描写的是知青王二与队医陈清扬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。作品很多地方写法超前,在那个年代,如此前卫、特立独行,招致非议是必然的。所以,在王小波生前,很多评论对其作品价值褒贬不一。王小波也曾说:“这本书的很多写法不但容易招致非议,本身就有媚俗的嫌疑”。但是读过之后,才知道作品对现实的批判和嘲讽,对人生存状态的反思,对人性自由和本真的彰显,迥异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知青小说。
大道至简。书法,拒绝秀逸,才能向往浑朴;追求典雅,必先脱离庸俗。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语句极其朴实,毫无矫饰,也正因如此,这些最朴素的词句铺排才能一语中的,入木三分。读他的文字,让人体会到现代汉语小说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。
在中国当代作家中,一旦说到王小波,必然会将之与卡夫卡联系起来。卡夫卡的作品,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涵义,是对深层次的理性、自由和个人生命的张扬。从《黄金时代》这部作品中,我也读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价值含义。
书中有一段写道:“我听了这话,觉得奇怪。我不应该因为尖嘴婆打了我一下而存在,也不应该因为她打了我一下而不存在。事实上,我的存在乃是不争的事实。……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悟到,犯不着向人证明我存在。……我发现我不能顶三个妇女,尤其是腰疼时。这时候我真想证明我不存在。……陈清扬对此极为满意。我也极为满意。在这种时候,我又觉得用不着去证明自己是存在的。”这段文字反复出现“存在——不存在——存在”。第一次读到这里,感觉很“荒诞”,而这种“荒诞”卡夫卡文学作品中也很容易寻到踪迹。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、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。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,但人可以在原有存在的基础上自我塑造、自我成就,活得精彩,从而拥有意义。而《黄金时代》的男女主人公王二与陈清扬的故事,不就是表达了痛苦、热情、需要、模棱两可、暖昧不清、荒谬、动摇的存在吗?事实上,从一开始,陈清扬就自己将自己异化,没有了归宿感,认为自己是这个人类社会中的“外人”,“魂不守舍,几乎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”。因此,陈清扬想找人证明的目的,就是要摆脱这种忧虑和恐惧。而正是这种忧虑和恐惧,才揭示人的真实存在。
“荒诞”是卡夫卡的思维特点,也是他的重要艺术秘诀之一,就是在他的创作中构成了一种“黑色幽默”式的悲喜剧情趣,比如他在《城堡》中描写,主人公一心想进城堡,不过想开一张临时居住证,奋斗一生而不得,当他奄奄一息,不需要它的时候,却又给他了!再比如《法的门前》中那位乡下人,到快死的时候,又说这大门就是为他而开的。卡夫卡的这种“黑色幽默”随处可见。而同样的,在《黄金时代》中,有这样一段话:“以前人家说她是破鞋,说我是她野汉子时,她每天都来找我。自从她当众暴露了她是破鞋,我是她的野汉子后,再没人说她是破鞋,更没人在她面前提到王二。大家对于这种明火执仗的破鞋行径是如此害怕,以至于连说都不敢啦”。这样的文字与卡夫卡《城堡》如出一辙。王小波在《黄金时代》中将 “黑色幽默”运用自如,这种黑色幽默”就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。
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说:“只有与他人交流时,他才会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孤独的,从而看到希望”。所以陈清扬找了王二,而从王二的角度来看,又何尝不是?《黄金时代》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,“假如我知道她有这样的打算,也许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”,还有一句,“可是我偏让她失望。”说明了主人公王二就是整个“麻烦”的制造者,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说:“一个人在世界上必须同其他人打交道,他和其他人的关系就是'麻烦'和'烦恼'。” 人的存在同人的选择以及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是分不开的。或许,王小波通过《黄金时代》这部作品,想表达的思想,就是萨特所说:“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?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,通过自由承担责任,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,也体现了自己。”
王二与陈清扬,不就是通过对方达到体现自己的存在吗?
王小波在《黄金时代》中写道:“陈清扬说,人活在世上,就是为了忍受摧残,一直到死。……这就是所谓的真实。真实就是无法醒来。那一瞬间她终于明白了在世界上有些什么,下一瞬间她就下定了决心,走上前来,接受摧残,心里异常快乐”。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,人之所以痛苦,是因为人同他的自下而上条件相脱节,面对着的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,即是一个荒诞的世界,人永远只能人有自我选择和自我控制的自由,忧虑、恐惧使人通向存在,只有存在,才谈得上自我选择的自由,它与光明和快乐相联系。所以,王二和陈清扬选择了反叛,书中所有一切的离经叛道,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。如加谬所言:“我反叛,因此,我存在。”
关于王小波,他被誉为“中国的卡夫卡”,确实,无论是作品思想、文字风格甚至是英年早逝都是如此相似,但在我看来,却又如此不同,卡夫卡的作品每一部都是如此沉重,甚至略带阴暗,结局也往往都是悲惨的。而王小波的作品,往往以一种戏谑的语气表达对社会对于生活甚至对一个时代的嘲讽,读起来轻松幽默,结局也似乎并不是很悲惨,卡夫卡的存在主义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味道,而王小波的作品甚至带有一丝浪漫主义色彩,他的作品,可读性极强。
初读《黄金时代》,我只是被它的故事吸引,回过头来细细品味,发现作者表达的目的并不是要诉诸你的情感,而是要激发你的理智,寻求人性与天地的本真。然而,当你再一次翻开书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刻苦铭心的生存体验,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生命呼叫。我想,这正是“见自己,见天地,见众生”的过程吧。
康复医学科:徐珺